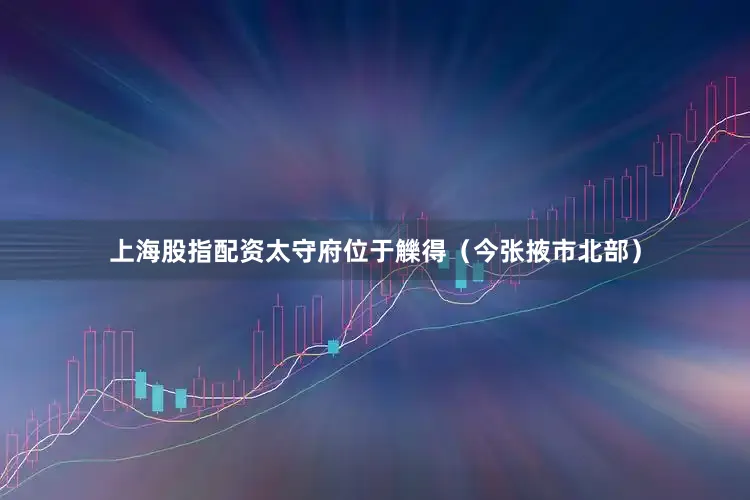
甘肃省的地形轮廓形似一只杠铃,两端宽广而中部收窄,而张掖正巧坐落于这条“杠铃”的中间位置,成为连接东西的枢纽。
在汉武帝时期,名将霍去病连续发动猛攻,冲击河西走廊的匈奴势力。匈奴浑邪王率领大批部众投降汉朝,被封为漯阴侯,赐予食邑一万户,成为汉朝的重要藩属。
汉朝在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、朔方和云中五个郡设立了五个属国,统称“五属国”,安置了四万余名匈奴降卒。随后又有二十多万匈奴部族陆续从河西走廊迁入,使这五个属国人口和兵力不断壮大,成为汉朝源源不断的兵员和战马供应地。
这五个属国相隔数百里,彼此联系逐渐松散,有利于汉朝实施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。属国周围水草丰茂,适合游牧生活。汉朝派遣属国都尉驻军,负责管辖与防务。日后汉朝频繁调遣这些匈奴骑兵,征战西域边疆。
河西走廊地广人稀,水草丰盛,非常适合畜牧业发展,拥有丰富的牛羊骏马资源,是天下名闻遐迩的畜牧重地。河西走廊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,阻隔了羌人的入侵,也阻断了匈奴的南下。汉朝相继设立酒泉郡(前121年)、张掖郡(前111年)、敦煌郡(前111年)和武威郡(前101年),合称河西四郡。
展开剩余81%失去河西走廊的匈奴人哀叹:“祁连山失去,我的六畜无法繁衍生息;焉支山失守,我的妻女失去了颜色。”其中焉支山又称胭脂山或燕支山,东西长约34公里,南北宽约20公里,主峰百花岭海拔约3978米,向南眺望时看不到祁连山顶的积雪,误以为张掖是江南之地。
焉支山屏障住北方的黄沙和寒风,使得焉支山与祁连山脉之间的区域山光水色交相辉映,翠绿连绵,成为马匹生长繁衍的理想环境。这里的气候比河西走廊其他地方更为舒适,居住于焉支山脚下,不觉寒冷刺骨。
河西四郡从东至西依次是武威郡、张掖郡、酒泉郡和敦煌郡,共辖三十五个县。扣除二三十万迁入内地的匈奴部族,新增中原迁移人口,户数达到七万余户,总人口约二十八万。张掖郡首府觻得(今张掖甘州区)辖十县,户数为两万四千余户,人口约八万八千。
张掖郡地处原浑邪王故地,位于弱水(今黑河)绿洲及其下游,直通居延泽。朝廷寄望“张国臂掖,以通西域”或“断匈奴之臂,张中国之掖”,故命名为“张掖”,其中“张”意为伸展,与张姓无关。
祁连山脉的溪流如大马营河、童子坝河、洪水河、黑河和梨园河等奔涌而下,汇流成黑河,形成了广袤肥沃的黑河绿洲,张掖城区就坐落在这片沃土之上。
张掖郡设有一座太守府及三处都尉府,太守府位于觻得(今张掖市北部),居延城建于北部居延泽附近,设居延都尉;在弱水中游建立肩水金关,置肩水都尉;焉支山下建立番和城,设农都尉。
西汉时期,农都尉主管屯田牧马,保障远征漠北及西域汉军的粮草和战马供应。大致而言,焉支山东部以屯田为主,今金昌市即由此发展而来;焉支山西部以牧马为主,形成现今著名的山丹马场。
山丹马场位于焉支山麓,总面积达2190平方公里,是中国最大的马场。盛夏时节,雪山为背景,蓝天白云,碧绿草原与花海交相辉映。骑马纵横草原,迎风把酒,令人心境开阔,感受天地间的浩瀚与心灵的纯净。
山丹马体态匀称,结实健壮,性格勇猛,耐粗饲,适应环境能力强,兼具速度与耐力,既是优良的驮马,也是良好的骑乘良驹。
公元607年(隋炀帝大业三年),隋炀帝开始巡游全国。八月初旬,天气渐凉,隋炀帝留下楚国公杨素镇守京城,率领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向榆林进发。天下富庶,物产丰盛,宫廷器皿豪华奢侈。随行军队五十余万,战马十万匹,粮草辎重沿途铺陈,千里不断。龙旗遮天蔽日,凤盖辉映华光,帝王御车如水流,战马奔驰如蛟龙。
夜晚,隋炀帝登高远眺,只见灯火连绵数百里,营帐星罗棋布,宛如天上繁星。每到一地,郡县献上的食物与特产堆积如山,炀帝召集群臣赏景饮酒,赋诗作乐,场面极其壮观。
隋炀帝西巡至河西走廊,驻跸于燕支山。高昌王麴伯雅、伊吾的吐屯设(地方监督官)以及西域二十七国的国王和使者在途径之处恭敬拜谒,场面盛大非凡。
西域各国因实力强大互相尊重,但面对隋朝军威威风,皆心生畏惧,齐声欢呼“万岁”。隋炀帝广泛招揽胡姬,乐而忘返,百官苦苦劝阻才肯回京。
这场在张掖举行的盛大会,让隋朝的声威达到巅峰,俨然成为万国来朝的盛况。只可惜隋炀帝铺设的宏大格局最终导致国破家亡。有人评价隋炀帝“罪在当代,功在千秋”,如其开凿大运河的功绩,实属实情。
唐朝时期,甘州即今张掖,肃州即今酒泉,甘肃省的省名便由甘州和肃州二地名称合成而来。
发布于:天津市新玺配资-炒股平台配资-实盘配资公司-按月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